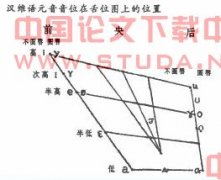一)开展学术评论,批评剽窃、伪科学和吹嘘等不良学风
我国原本有良好的学术评论传统,且都是指名道姓的。例如1935年唐兰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自序中说:“在本书里不免要批评到许多学者的错误。这里面很多是著者所敬服的前辈和密切的朋友。就如罗振玉先生,他对于著者的学业,曾有不少的鼓励。他的一生著述和搜集材料的尽力,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甲骨学可以说是他手创的。但他那种考释文字的方法是著者所不能完全同意的。……郭沫若氏曾告诉我‘昔人有一字之师,今人有一语之敌’。不过,治学问而不敢明是非,还成什么学问。学问本只是求真理。我们找出自己过去的不是,指摘别人的不是,同样,也愿意别人指摘我们的不是”(见该书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第11—12页)。这是何等可贵的学风啊!
王力在《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所刊文《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曾批评著名的语言学家傅东华。非常遗憾的是,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严重损坏了批评和批判的名誉,以致文化大革命后我国语言学界很少展开学术评论,尤其是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即使有星星点点学术交锋,读者也如堕五里云雾,不知是针对谁的哪本书而发。这十分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破就是立”固然不对,但“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塞不流,破中有立”还是合乎辩证法的,应大力提倡。在这方面,夏渌教授专为批评康殷对汉字源流的种种错误解释而写的厚达 493页的著作《评康殷文字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夏书出版以前,《光明日报》等报刊曾发文,对康书进行了不少无原则的宣扬,该书竟成了市场畅销品,使不少读者从康书得到错误的知识。遗憾的是同外国相比,学术批评的著述在我国少得可怜。当然,我们充分肯定夏先生十年来带头写学术批评专著的功劳,并不等于说夏先生对每个字的解释都无懈可击,我们也不应对批评者提出这种苛求。
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开展学术评论和批评方面,我们要向外国学习。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 )曾指名道姓地批评美国的社会语言学家,说他们所做的工作类似收集蝴蝶标本。[①a]他们也指名道姓地对乔姆斯基进行了反驳[②a]。美国著名语言学家H.阿斯勒夫、C.F.霍凯特(1916— )、R.A.霍尔(1911— )都比乔姆斯基大十几岁,照样对乔姆斯基的著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①b]
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有人用种种理由反对进行学术批评,其中之一是长辈不宜批评晚辈或相反,晚辈不宜批评长辈。还有人认为,无名小卒不应批评名人,因为我国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这些错误观点严重影响了我国开展学术批评,不利于学术进步,因为学术只有在交锋中才能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还有人认为批评文章没有学术价值,这也是不对的。上面提到的霍尔写了一本著名的书《语言学和伪语言学》(JohnBenjamins出版公司,1987年),它就是霍尔进行学术批评和评论的12篇著名论文的汇编,在国外语言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对待批评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在其名著《哲学研究》的前言中坦率地说:“自从我在十六年前重新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以来,我不得不承认我在第一本书里所写的东西中的严重错误。在弗兰克·拉姆塞逝世前两年的时间里,我和他作了无数次谈话,他批评了我的想法。他的批评帮助我认识到这些错误——这些错误之深是我很难估计的。这些批评是强有力的、确定无疑的。不仅如此,我还要感谢本校教师斯拉法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思想所作的不间断的批评。我要为这本书的一些最重要的思想感谢这种激励。”(见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第145页,三联书店,1988年。)
要开展学术评论,除开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外,首先要大力开展的应是对不良学风进行严厉的批评。学风的好坏是关系学科存亡的大问题。在学术观点上尽可各抒己见,甚至可以从始至终坚持各自的观点,但是在学风问题上是绝不能让步的。尤其是现在已蔓延成风的抄袭剽窃现象,如不刹住,以假乱真,假作真时真亦假,一般读者分辨不出是非,假的著作竟然不断获奖,致使有人觉得这是条获取名利的捷径,这将给严肃的科学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甚至会坑害一代乃至数代青年人。
有人为自己的抄袭行为辩解,说“我抄袭时出版法还没有颁布”。这条“理由”不能成立。早在1920年梁启超在叙述清代的学风时,曾谈到清代正统派的学风的特点,其中有两条是:“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②b]198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言漫话》刊登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已故研究员王伯熙的文章《抄袭剽窃,文败名裂》,其中指出“汉朝人因循抄袭的陋习就已经相当严重。”他举了两个例子:晚清的一个会元和一个翰林因抄袭别人的文章虽然一时获得非分的名誉,却终于文败名裂。王文中引了韩愈(768—824)的话“维古于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可见早在唐朝就有人谴责剽窃,哪里需要等出版法才能认识到剽窃是恶劣行为呢!上引唐兰著《古文字学导论》引言中也指出:“坊间虽罗列着许多……论著,多数是那班一知半解,或竟全无常识的人所剽窃抄纂的,这当然不会有一贯的理论”。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谭永祥在其《修辞精品六十格》(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1994年山西第一次印刷)中揭露《修辞学纲要》(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抄袭他的《修辞例说》《修辞新格》(连同原书的错误);他并引用台湾龙应台女士的话:“温柔敦厚做人或许是好的,但做事、做学问,却是极度不可取的。”谭永祥在其“《修辞新格》增订本后记”中指出:该书“十五个新格,就被《修辞学纲要》抄去了十个,包括新格的名称、定义,连同例句和解说全都‘照单全收’”。不过《修辞学纲要》多次提到谭永祥新立某某格,所以性质同全面剽窃还是有所不同。
《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61—262页的一段,第262的一段连其脚注⑦⑧(在该书第311—312页)原封不动地抄拙文《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第204—207页);该书第257—260页第2节“成语的文化背景”大段抄南开大学中文系向光忠教授的《成语与民族自然环境、文化传统、语言特点的关系》(刊《中国语文》1979年第2期第135—139页),均未注出处。这个责任当然主要应由该章节的编写者担负。该书对前人关于语言和文化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是该书的优点。[①c]
许威汉的《训诂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虽然在后记中注明“因为它是用为教材的,为讲述方便(?),引用陆宗达先生、周大璞先生等著作及其他有关训诂论述中不少例说,未能注明出处,特此说明”;但实际上,抄袭的远非例说,也远不限于陆、周二人。例如,许书分论第一章“训诂术语”第47 页、60—64页从内容到文字表述及例子都抄自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所作《谈训诂学术语的定称和定义》(刊《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全不注出处。许书第133—135页关于词义引申的类型只是提到“兹略参照陆宗达的说法”;其实,许书关于词义引申的分类及部份例子基本抄自陆宗达和王宁合著的《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许只字不提此书和王宁,是不好的。[②c]《光明日报》1995年11月1日发表的程黧眉的文章指出:“偷别人的作品与偷别人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要想写出好作品,首先要有好的品德;否则,东抄西抄毁了自己的文,也毁了自己的人。”这是很有道理的。李广田说:“人失真,无人格;文失真,无风格”(见《李广田散文》第1卷第10页,1994年)。针对目前的学风,最后二字可改为“文德”。
不良学风的第二种表现是伪科学不仅渗透到自然科学领域,也渗透进语言文字学。武汉大学中文系夏渌教授给我的信中写道:“东北出版了李蕴的《象数文字学》,并有名家作序,誉为‘另辟蹊径’,但实际是把《说文》解析某一字的字数,主观定为该字‘仓颉造字’的‘天机神数’,他得此天机,能破译全部甲骨文、金文。
“山东某大学某教师,吹嘘得到了‘破译甲骨文的密码’,从而认识了全部甲骨文。传媒广为宣传。
“把算命拆字的迷信和‘军事密码’之类的不相干的东西,套到古文字学科上,大搞神秘主义,以欺世盗名,报上竟大加宣扬,出版社竟准备逐一出版。本是人民群众造字,何来‘象数’和‘密码’?甲骨文三分之二以上,是未见于《说文》的,何得以《说文》有的某字字数,作为解开甲骨文的‘数字值’和‘密码 ’”。
“卖假药、假酒害死人,社科领域搞唯心主义的假科学,流毒青年和群众,同样害人不浅,该谁来管?社科领域也存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问题,‘打假’的问题。”“文科、社科组织既涣散,学会组织也不够严密,四川成都青羊宫的假《周易研究》为名算命诈骗案就是典型事例。神秘主义、蒙昧主义的东西,往往打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幌子,真假难辨,受害者惑于国家单位的支持,名人的吹嘘,‘国王的新衣’往往能风行一时,无人揭穿。学术界正气得不到扶持,歪风邪气插上名利的翅膀,如虎添翼,得心应手。实际上也存在一个社科研究的体制问题,领导和监督的问题,公开讨论的场所问题。”
语言学界的伪科学最恶劣的表现是徐德江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本错误百出的书和他在《汉字文化》上发表的一些同样是错误百出的文章。对此我已在拙文《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驳云林[出版徐德江坏书的科学出版社的责编王人龙的化名]的一些错误观点》(刊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教学》 1995年第2期)和《不要胡批索绪尔——评徐德江书文的一些错误》(刊大连外国语言学院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年第4期)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蜚声给我的信中指出:“学术界的骗子等于盗贼,与出版社串通一气,是贪污腐化的一个变种”。天津师范大学外语部英语副教授顾钢在读到我的上述两篇批评徐德江和王人龙的文章后给我来信,指出:“现在学术界不是有没有骗子的问题,而是骗子有多少的问题。目前,急功近利的社会思潮孕育了一批骗子,其中不乏学术骗子。与别的骗子相比,学术骗子的隐蔽性和危害性都更大。他们往往拉大旗作虎皮,把质量低劣的‘学术’作品推向社会,骗取名利。在学术骗子中,靠剪刀浆糊欺世盗名的骗子自然可恨,那些自我标榜有‘创见’的骗子更加可恨。他们传播错误的观点,贻误一代青年。过去几十年才造成一个大师,而今天似乎一年就可以出许多大师。学问似乎越来越容易做,因此对这种毒化学术界的骗子必须给予毫不留情的鞭挞。”
不良学风的第三种表现是自我吹嘘和互相吹捧。自我吹嘘最恶劣的事例是自封为教授的徐德江,把他错误百出的观点自我吹嘘为“徐德江公式”、“徐德江学说”、“徐德江理论”。对此我已在拙文《80年以来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回顾和反思》(刊《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4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徐德江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将这种吹嘘进一步升级。徐德江在他任实际主编的《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第33页借法国一名汉语教师白乐桑之口,吹捧在巴黎举行的第27届国际汉藏语和语言学会会上他的连文题到内容都错误百出的发言《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言》[①d]“对汉语、汉字理论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其实,巴黎会议上一百余人都不屑于听他的发言,只有四个人参加轮到他发言时的会议:两个是分组会议的主持人,一个是台湾的学生,一个是我。我是专为批评他的发言而参加该分组会的。(详拙文《学术讨论时不应谩骂——兼评〈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的几篇文章》[①e])。接着徐又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 3期第49页自我吹嘘,说:“他……的论著……代表着当代[②e]汉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遗憾的是,类似的无原则吹捧并非个别。海南大学教授鲁枢元的《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在语言学方面错误百出,严重歪曲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思想,还有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我已写了两万五千字的长文《要运用语言学理论,必须首先掌握语言学理论》(刊《北方论丛》1996年第5期),对该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该书责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白烨尽管在该书序言中说他读该书稿时,带着挑剔眼光,却根本没有看出这些错误,相反在该序中吹棒鲁枢元具备“真诚的治学品格”,该书“是一部在角度上、立论上、语言上都卓有特色的好书”,“很光彩耀人”,并称赞鲁君在“语言学上”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称他为“理论家”。
《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发表的韩少功致鲁枢元的信,竟吹捧鲁的错误百出的《超越语言》为“快餐式的十全大补”“有里程碑意义”。
申小龙的自我吹嘘也令人作呕。他居然说“中国文化语言学……对汉语的本体论和研究方法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系统的新学说”(见他为他主编的《文化语言学丛书》[实际只有四本]写的总序)。苏新春竟赞同这种自我吹嘘(见戴昭铭主编的《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北方论丛》丛书,1994年]第27页)。1995年10月5日《光明日报》第七版以首篇位置发表胡以申的文章,也对申小龙的所谓“文化语言学”进行了无原则的吹捧,说他“在‘文化语言学’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我在拙著《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38—39页等著述中早已多次指出,从语言看文化,是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语言古生物学和词与物等学派早已研究过不知多少遍的老课题,因此,提出“文化语言学”这个新术语,并不等于开创一门新的学科。即使就我国来说,现在这些所谓“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拓者所谈到的许多内容也早已是我国的训诂学著作探讨过的问题。例如,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三章就详述了“《说文解字》中所保存的有关古代社会制度、生产、科学、医疗学的资料”。陆著《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年)也有专节“通过训诂了解和研究古代社会及其科学文化”。因此,申小龙等将所谓“文化语言学”称作“新学说”,这就像俄谚所述,无异于“发现了已被发现的美洲”。
不正学风的第四种表现是一稿多投。申小龙数年内出了20多本书,有一些是大同小异的内容(包括抄袭他人著作的部份)经过重新组合或改头换面,用不同的书名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
关于学风,我国朴学有良好的传统,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已故张舜徽教授在其《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前言中有一段话谈到乾嘉学派中“有的学者,甚至将毕生的心思才力,投入一部书的深入钻研。当时朴实治学的精神,形成了风气,各效所能,写出了不少专著,留下了丰富成果,给予后来研究古代文字和整理文献遗产的人们以莫大的方便。这种成绩,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而不容湮没。”反观我国现在个别中青年,可能是受我国目前商业界出现了一些暴发户的影响,急功好利,写书和写文章,往往粗制滥造,信口开河,甚至抄袭剽窃,不以为耻,反倒批评别人“急功近利”(见下引《中国文化语言学》第166页),并且用一些歪理为这种行为辩护。例如申小龙在《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65—167页)居然反对“立论(要)无遗漏地寻找经验材料的‘证实’”,鼓吹“‘痛快’、‘偏颇’之论往往是至理名言,真知灼见”,“一些新思想的提出,其意义并不在于考据(?),而在于振(申误作“震”)聋发聩”;申甚至“鼓励冒险”,活脱脱地流露出一种急于求名的心态。《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陈冬生等三人的文章《树立科学的现代争鸣意识》竟然同意这些谬论,将它奉为“科学争鸣意识”。
近年来,在开展学术批评方面起了良好带头作用的刊物有《中国社会科学》《福建外语》《外语学刊》《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湖北大学学报》《现代外语》等。《北方论丛》虽然发表了大量文章,对申小龙进行无原则的吹捧,但也发表了一些批评他和其他人的文章。根据不精确的统计,在语言学和文字学方面发表批评文章最多的刊物是《福建外语》和《北方论丛》。遗憾的是某些语言学刊物对上述种种不良学风几乎是不闻不问,仿佛身居世外桃源。这只会助长语言学界的这股浊流继续泛滥。没有强大的学术批评,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徐德江的错误百出的所谓论文竟然收进《小学新实验课本·语文》的“教学指导文选”(见《教学实验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09页,1994年),流毒甚广。后果之二是台湾新学识文教出版社竟要求购买申小龙的全部著作的版权(见申小龙:《语文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前言”第10页)。这只会影响我国大陆的语言学声誉。《光明日报》1995年10月12日第2版的头条新闻“艺德建设是文艺界的重要课题”。我觉得,这一精神同样适用于语言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
从这些年来上述种种乌烟瘴气的弥漫,我们应得出深刻的教训:学风的衰败,固然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在学术界的反映,另方面也因为我国大学教育中仅注重知识的传授,严重忽略了文德和学风的教育。建议我国大学将宣传出版法、遵守出版法、尊重他人劳动作为大学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或者在大学德育中包括上述内容。要使全体教师和学生认识到,著述(包括毕业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中的抄袭和剽窃行为,其性质如同考试作弊,是应受到严厉的制裁和处分的。
徐纪敏在《科学学纲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1,493页)指出:“科学家的业绩表明,道德之光常常燃起智慧之火,而一切道德堕落的人必将走上与真理相违背的道路,从而毁灭他科学的生命”。
这些年来不正学风蔓延,除当今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外,有关出版社也有一定责任。他们中的某些人或不熟悉语言学专业,或审稿不严,或一窝蜂地就相同的选题(如“文化语言学”)向同一个中年作者约稿,致使他不得不走上剪刀加浆糊的错误道路。
(二)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中外古今偏废任何一方,都可能给我国语言文字科学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唐兰在上引《古文字学导论》(第28—29页)上说:“近来学术界有一种风尚,崇信异国人所做的中国学术研究,而把自己的专门学者看成‘东家丘’。异国人的治学方法,可以钦佩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他们也有所短。即如语言和文字两方面,语言声韵是他们所能擅长的,文字训诂却就不然。有些人瞧见异国人对语言声韵研究得很有些成绩,就去推崇这一类学问,因之文字学就不被重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这是很有道理的。遗憾的是他的这些话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加之陈伯达一度推行错误的“厚今薄古”的方针,以致我国在一个时期曾将传统语言学,尤其是文字学和训诂学的研究打入冷宫。打倒四人帮,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局面才有所改变。这个教训值得深刻记取。然而,对我国传统语言学,包括训诂学的重视还是很不够的。我国和北师大最早的博士生导师、被誉称为章太炎黄侃学派奠军、学富五车、著名的国学大师陆宗达教授(1905—1988)所著《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年)和《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年)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出版的最早的两部传统语言学著作,对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复兴,起了很好的带头和推动作用。《说文解字通论》在痛斥四人帮污蔑《说文解字》为“尊崇儒家,反对法家的典型著作”之后,用一章篇幅客观地指出了《说文解字》的巨大成就和局限性;因此这两部书培育了打倒四人帮后的几代学人,是高等学校传统语言学的重要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我本人从中受益极深。正是受这两本书的启发,我才得以发表七篇“比较词源学”的论文。
厚今薄古的思潮至今仍有反映。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语文建设》1995年第8期用显著位置发表的文章“语言文字工作的旗帜”。该文正确地呼吁进一步推行简化字、推广普通话、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正确地批评了反对这一方针的个别人,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人“在选择第二语言、第三语言时,汉语排在第五位、第六位”,[①f]这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但与此同时,该文说:“现代化既有建设力量,又有破坏力量……回想近代中国语言文字的几次前进,是不是破坏呢?白话文就破坏了文言文,横排就破坏了竖排,挡都挡不住。现代化也是一种革命,它是不买你的帐的。你死抱着国粹,它就把你扔掉拉倒,什么国粹都没了。……用简化字还是用繁体字,是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谁影响谁的问题。我们先进,为什么要向落后看齐?”在我看来,这段话有以下几点欠妥:(1)五四运动后,白话文只是取代了文言文作为广泛使用的书面语言的地位,并没有破坏文言文。白话文是文言文的继续,二者之间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有许多相同的部份,前者从后者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至今文言文还是中学、特别是大学,尤其是中文系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钱钟书还用文言文撰写了有很大学术价值的四卷巨著《管锥编》。不学文言文,就无法研究、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的文化;即使是当今的文人学士,不学文言文,就无法从根本上提高运用书面语言的能力。现代优秀的白话文作家,几乎无一不具有深厚的文言文功底;(2)横排与竖排只是印刷排版的问题,同“中国语言文字的几次前进”是两回事,何况现在横排并没有破坏,也没有必要破坏竖排。我国大陆的图书固然绝大部分改为横排,但报纸的标题既有横排,也有竖排,可见竖排并未被破坏。(3)什么叫“国粹”?《现代汉语词典》对“国粹”的解释是“旧时指我国文化中的精华(含有保守或盲目崇拜意味)”[②f]。笼统地说“谁死抱着国粹,它(指现代化)就要把你扔掉拉倒”,很容易挫伤至今仍在学习和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许多人的积极性。也许该文所说的“国粹”是指繁体字?那也很不妥当,关于这点,下面我即将谈到;(4)说“用简化字还是用繁体字,是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或把繁体字说成是“国粹”,很不恰当。一是我国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人至今还在广泛学习和使用繁体字;二是江泽民同志1992年12 月14日明确指示“海峡两岸的汉字,当前可各自维持现状(指台湾可继续写繁体字);……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写繁体字,还是写简化字,应尊重作者的风格和习惯,可以悉听尊便”;因此把用繁体字说成“落后”、“国粹”,很容易伤害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使用繁体字人的感情。何况台湾尽管政治上落后,其经济和技术在某些方面并不落后,我们还在不断地引进台资,因此笼统地说“我们先进,为什么要向落后看齐”,似乎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对台政策。
另一方面,对待外国语言理论至今也有人持排斥态度。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1)申小龙竟然断言:“西方语言理论及其方法基本上不适合汉语的文化特征”(转引自戴昭铭主编《建设中国文化语言学》,第24页,《北方论丛》丛书,1994年,哈尔滨)。且不说“汉语的文化特征”的涵义不明;其实,申小龙自己的实践同他的这一见解也是相左的。他的《语言的文化阐释》(上海知识出版社,1990年)大量抄袭了国人介绍或翻译的外国人的著述。
(2)《修辞学习》1995年第2期发表了拙文《修辞学在西方认知语言学中有跃居首位的势头》,接着该刊第3期发表了复旦大学教授宗廷虎的文章《汉语修辞学21世纪应成为‘显学’——读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札记》。我们的这些论断是根据西方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现状做出的。看不到原著的读者不妨参看《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3期所刊赵艳芳的文章《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上述说法绝非信口开河。《修辞学习》同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显学”问题的思考》。对这个问题进行学术讨论,是好事。遗憾的是该文给宗文扣上了“把老祖宗丢在一边”“凡事‘言必称希腊’”“以洋律中”等莫须有的帽子。宗廷虎在其《再论汉语修辞学21世纪应成为‘显学’》(刊《修辞学习》1995年第5期)已对该文进行了正确的反批评。我国对外开放、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不到二十年,我们对外国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包括修辞学理论)不是知道得太多,而是太少太少,因此上述帽子很不合适,不利于在宏扬祖国语言文字科学优良传统的同时,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把我国的语言文字科学推向前进。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言必称希腊”,是针对当时的教条主义者照搬外国革命经验,不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用那时的批评针对我国今天的语言科学研究现状,很不恰当。
此外,从根本上说,笼统地反对“以洋律中”,是不正确的。世界上的语言虽然有民族特色,但是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语言的共性通常大于个性,这正是不同语言均可互译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详见前面提到的拙文《要运用语言学理论,必须首先要掌握语言学理论》)。在修辞方面,共性更多。我们所知的语言都有共同的辞格就是明证,只是辞格的表现方式往往因语言而异。关于语言中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于全有的文章《语言研究的个性和共性与文化语言学的价值取向》(《语文研究》1995年第3期)说得很好,可参看。关于语言研究中的各种关系,王宁教授给我的信中说得很好:在当前语言文字研究中,“忽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导研究,把现实与历史对立起来的有之;把国内与国外对立起来的有之;把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的有之;把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的也有之(按后一对立是申小龙观点的主线——伍)。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杨自俭教授在《山东外语教学》1995年第1期所刊《关于语言研究的几点想法》说得也很好:“语言研究要处理的关系主要有外国的和中国的,历史的和现在的,理论的和应用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在处理这几种关系上我赞成走中庸之道,就是说要两者并重,或者叫两手抓。我们所走过的弯路、所犯的错误,差不多都是偏离了中庸所造成的,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真理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科学的进步依靠处理好矛盾双方的关系”。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沈家煊给我的信中写道:“目前某些从事汉语研究的人有过份强调汉语特点的倾向,对语言的共性注意不够。有些人甚至认为汉语是十分特殊的语言,跟世界上其他语言都不一样,西方已有的语言理论对汉语根本不适用,使研究者误入歧途。这是一种很狭隘的观点,既不利于汉语研究的发展,也不利于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对国外已取得的成果借鉴不够,过分强调汉语的特殊性,用西方语言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种老生常谈来代替严谨的科学研究。这是在走回头路,不是前进。”
可能是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曾经实际上推行过闭关锁国的政策,也由于我国汉语界的许多教师和研究工作者不能阅读外语原著,以致我国语言学界某些人仍对外国理论采取排斥态度。而且,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在一部份人中间,越是外语不好,越有排外情绪。当然,我国有些懂外语的人在介绍国外理论时有时没有选择精华,深入浅出,结合汉语实际,致使有些人觉得外国理论深奥,高不可攀,也有一定责任。其结果是现在海外华人(包括从大陆移居海外的学者)在借鉴外国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方面,有些人已走在大陆前面。在我国大陆出版的他们的著述有:(1)美籍华人屈承熹著:《历史语法学理论与汉语历史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2)美籍华人戴浩一、薛凤生主编:《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同上出版社,1994年);其作者大部分为美籍华人;(3)南开大学石锋编《海外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文出版社,1994年,其作者大部份是我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移居海外的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叶蜚声教授给我的信中写道:“适用于汉语分析的国外新理论,一般总是在国外首先试用。各国都有研究汉语的队伍,以华裔学者占多数。他们的研究动态和成果,往往为我们所忽视。他们身在国外,最了解国外的新理论,并且抢先使用于汉语,他们的著作反映出哪些理论适用于汉语,如何应用,成效如何。了解这方面的动态对我们有直接的参考作用。必须有专门的单位加以关注,每年作出综合的介绍。”
造成上述后果的原因很多。除大陆人材流失这一客观原因外,另外的原因是大陆部份学者认识上有上述偏差,我国大学中文系对外语和学习外国语言学理论不够重视,外语系则很少传授我国传统语言学知识,以致这两个培养语言学工作者的主要部门都有偏废一方的缺点。杨自俭教授在为《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增刊》所写的“写在前面的话”中也正确地写道:“从全国看,外语教师普遍不注意提高自己的中国语言文化水平,很多人不懂得,中文水平上不去,外语水平也不易上到较高水平的道理;学中文的教师普遍不注意提高外语水平,很多人不懂得恩格斯所说:‘要了解本族语言的材料和公式,就必须追溯这些材料和公式的形成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一不顾本族语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各种活的和死的亲属语言,那末,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9页[我根据德语原著,对中译文作了订正——伍铁平])”。他在亚洲翻译家论坛论文《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中建议:“改造现有的中文系和外语系。在中文系提高外语的要求,在外语系提高中文的要求,都要突出中外文写作训练”。
值得大声疾呼的是,如果我们不正确处理好中外古今的关系,如果不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听任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懂外语的知识分子大批地或流向外企,或流向国外,或不得不大量兼任业大、夜大、函大、电大等基础课程,没有时间从事必要的科学研究,难以提高业务水平;加之离退休人员增加,脱离教学与科研工作,从事非专业性工作;其结果,不仅海外华人的研究水平有可能超过我国大陆,外国人对汉语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也可能超过我国。例如,美国的白一平(自取中文名,英文名W.H.Baxter[1949- ]著有922页的巨著《汉语音韵学手册》[①g](Moutonde Gruyter出版社,1992年),独联体的C.A.斯塔罗斯金博士(1953— )著有724页的巨著《古汉语音韵系统构拟》(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9年)。我没有读到国内外对这两本书的评价。不论如何,外国人能写出这样大部头的著作,其中总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没有看到国内这几十年出版过篇幅这样大的音韵学专著,这是我们应引以为愧的。
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据韩国来我校学习的博士生说,韩国教师的地位和待遇都很高,学生尊敬和爱戴自己的老师如同对待自己的父母,因此韩国人以当教师为荣。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派到我国学习的人数极多。仅北师大就有七十余人。除十几人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学习基础汉语外,其他都在中文系学习汉语语言文字学或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或民间文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种大规模地派留学生出国(均自费)的做法,必然大大提高韩国的学术水平。以人口比例计算,韩国派出的留学生的数目,比我国不知要超过多少倍。
(三)大力提高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文化水平和外语水平。
举几个例子说明现在大学教师知识水平滑坡的现象:
(1)有位大学教师在其《超越语言》中将俄国教育学家乌申斯基(1823—1870)误作“苏联教育心理学家”;该书还有许多有违语言学常识和其他常识的错误。另一位研究人员在其《当代跨学科语言学》中则将乌申斯基误作苏联语言学家。还有一个著名大学英语系获硕士学位的讲师多次将“不可救药”写成“不可救要”。
(2)有位大学的副教授在其译著《列维-斯特劳斯》中将英法之间的“多佛尔海峡”误译为“多佛尔大街”。申小龙在其《语言的文化阐释》第209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上原封不动地重复这一错误。两个出版社的编辑都未发现这一常识性的错误。
这类知识性错误也见于科研机关和出版社中的高层次知识分子的译著中。例如:(1)有位研究人员所译的杰利·罗杰瑞(自取中文名)的《汉语概说》,至少有20%以上是误译,而且加进了译者的一些原则性错误论断(如说“汉语方言是不同的语言”;“汉字不合国家改革的需要”),糟踏了外国学者的一本好书。详见拙文《翻译科学著作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刊《外语与翻译》1995年第4期)。
(3)《拉丁语汉语词典》(1988年,第400页)将拉丁语的penis(阴茎)译为“男性成员,男会员”,因为该词典是翻译《拉俄词典》的产物,在俄语中мужской член(阴茎)中的член有“器官”和“成员”二义。这种种被人们传为笑柄的错误都说明我国现在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素质下降。这类常识性的错误在文革前的出版物中较少出现,[②g]所以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大力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文化水平和外语水平。
鲁迅在《二心集》中说过:“语法的不精密,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句话说,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语文教育,包括语法教学,是提高人们整个文化素质的重要环节,万万不可忽视。现在社会上不少名流写文章,经常不区分语言和文字,就是因为缺乏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因此现在有些大学、特别是业大、夜大、电大、函大的外语系,又将语言学概论课程砍掉,是极不妥当的。
参考文献:
①a详《许国璋论语言》第197—206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
②a见戴尔·海姆斯《论交际能力》等论文,中译文刊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①b阿斯勒夫的批评见于他所作《语言学史和乔姆斯基教授》(刊美国《语言》杂志1970年第3期)。霍凯特批评乔姆斯基的学说“误入歧途,引入大量中世纪的僧侣哲学,致使语言学工作者舍本逐末,劳而无功”(见霍凯特为其《现代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写的序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计,1986年)。霍凯特和霍尔还有专著批评乔姆斯基,见后。
②b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①c该书内容方面也有一些错误。例如第261页上说:“西方语言,如印欧语系和阿非罗-亚细亚(闪-含》语系的语言,属于屈折型语言。这一类型的语言有着丰富的前缀和后缀”,这不对。第一,印欧语系中包含亚洲一些语言,不全是西方语言;闪-含语系的语言主要在非洲;第二,屈折语的典型特征不是有前后缀,这是分析语和粘着语也有的特点;第三,印欧语中的现代英语不属屈折型语言,而属分析型语言。
②c到了许威汉主编的《现代语言学系列》中的第二本书申小龙的《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6—205页,申只字不提许抄自陆、王书的许多段落、而仅提许,于是把陆、王的首创权都错误地归功于许了。
①d申小龙在上引《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第226页上居然肯定性引用徐德江的荒唐言论“文字是书面语言”。
①e刊《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②e请注意,连“中国”二字都没有,大概自认为是全世界的最高水平吧!
①f这对过高估计汉字和汉语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人,不失为有力的反驳。
②f其实这个解释并不全面,至今人们仍用“国粹”一词,而且有时用于褒义。如《语文建设》1995年第10期所刊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程祥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章,题目是“五洲华人弘扬国粹(指‘绝对求偶’)的盛举”。
①g原文是handbook。顺便说一下,有些英文词典对此词注为“smallbookgivinguseful
facts”,不确。H.c.Wyld的《英语通用词典》(1956)对此词的释义中没有small(小的)一词。
②g当然也非绝无仅有。例如查良铮所译普希金诗《致大海》竟将зыбь(涟漪、微波)误译作“牙齿”(俄语为зубы)